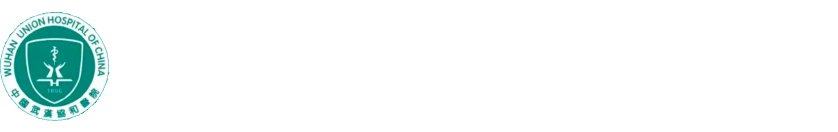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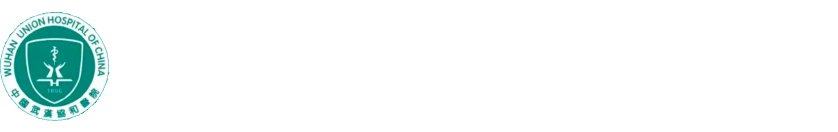



我是在汉培训一年的护士。一年前,我还是重症医学科的“小白”,面对危重病情时常手足无措,甚至感到害怕。但在科室领导和各位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得到了飞跃的成长。这一年的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,重症医学科的工作不止于解决患者生理上的疾病,更要用心关注他们的内心需求。如今的我,不仅能熟练处理临床病情,更懂得用专业与温暖守护每一位重症患者。由此我写下了这篇体会。
南丁格尔在《护理札记》中写道:“护理是一门精细的艺术,它需要比任何其他艺术更多的奉献、准备和清晰的认知。”在AI算法重构医疗决策的今天,这句箴言愈显其沉重份量。当监护仪的数据流淹没了指尖的温度,当预测模型主宰了病情的走向,我们是否还守护着护理最本质的内核——对生命最细腻的感知与最温柔的尊重?在ICU的那个漫漫夜班,一位乳腺癌晚期患者用她的挣扎,给我上了一堂关于生命尊严的必修课,让我在技术与人文的夹缝里重新审视护理的真正刻度。
她是一位乳腺癌转移至颈椎的术后患者,因咳痰能力弱,气管插管一直无法拔除。夜晚,她开始躁动不安。我靠近她,轻声询问:“阿姨,您是疼吗?还是哪里不舒服?”她用干裂的嘴唇,挣扎着表达着“口渴”。我赶紧小心翼翼地帮她漱口,用喷壶轻柔地湿润她干燥的口腔黏膜,又轻轻按摩她因长时间卧床而僵硬的四肢。这些护理细节,都是我从南丁格尔的《护理札记》中学来的,我坚信这些微小的举动能给患者带来一丝慰藉。然而,阿姨的躁动并未缓解,她不断摇动的头颅,让原本充盈的枕头陷出一个凹槽,我的心也随之揪紧。
无奈之下,我向值班医生求助。遵医嘱使用镇静药物后,我为她擦去额头上的汗珠,调整好枕头高度,阿姨痛苦的面容逐渐舒展,仿佛带着一丝微笑和满足,安静地睡着了,我才稍稍松了一口气。次日清晨,镇静暂停,阿姨再次躁动起来。恰在此时,家属来进行探视。几句简短的对话后,他们竟决定放弃治疗。面对这个决定,阿姨却对我露出了会心的笑容。那一刻,一股前所未有的无力感席卷而来。监护仪持续的滴答、呼吸机沉闷的运转、偶尔传来的痛苦呻吟,让我烦闷;我曾认真记录出入量、仔细调整输液速度、时刻监测生命体征,此刻却只余愧疚;我倾尽全力守护、试图给予慰藉的真心,在这个决定面前,显得如此苍白。我开始怀疑自己:如果再多一点耐心,能否减轻她的痛苦?能否改变这个结局?
......
在ICU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中,我们常常把“抢救生命”当成最高目标,却忽略了有些生命需要的是有尊严的告别,而非无意义的延长。阿姨摇动的头颅、渴望的眼神,现在回想起来,那或许是她无法言说的告别方式。当医学手段已经无法逆转病情,当导管和机器成为生命的延续,她是不是在用自己唯一尚能掌控的方式,坚守对生命自主权的最后主张?
南丁格尔把护理视为“将病人置于最佳条件下让自然发挥作用的艺术”。这个“最佳条件”,不仅指向洁净的病房与先进的医疗设备,更深植于对患者心理和精神需求的尊重。ICU护士需要敏锐的直觉,而非仅仅是服从。这要求我们:在精进技术的同时,涵养人文敏感度;在遵循规程的基础上,锤炼伦理判断力。从那以后,我在监测生命体征之外,更着意于患者的眼神、手势、微表情这些无声的信号;更审慎地考量治疗目标与患者意愿的契合。我们不只是医嘱的执行者、生命的守护者,更应该是患者声音的放大器、意愿的传递者。
未来,我会继续精进专业技能,更努力去倾听沉默,更用心地解读无言。在生与死的边界上,我要做一位兼具科学与人文的护理者。因为护理的真谛,不仅在于如何照顾生命,更在于如何理解生命——包括它的开始,也包括它的结束。

本文作者:陈鹏羽
在汉培训科室:重症医学科
.png)
文章打印